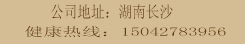![]() 当前位置: 丹霞山 > 丹霞山门票 > 青海作家写青海李成虎一个人浪漫地行走
当前位置: 丹霞山 > 丹霞山门票 > 青海作家写青海李成虎一个人浪漫地行走

![]() 当前位置: 丹霞山 > 丹霞山门票 > 青海作家写青海李成虎一个人浪漫地行走
当前位置: 丹霞山 > 丹霞山门票 > 青海作家写青海李成虎一个人浪漫地行走
李成虎
一个人浪漫地行走(节选)◆李成虎
垂眉尽览枯荣昪,
过眼烟云闭口长;
故迹知秋寒暑事,
新情对镜又连章。
以前我从种种渠道,对故乡风土人情、人文精神,抑或是胜景都有了或好或坏或多或少的印象。真正“到此一游”时,无非是印证了或失落了某种想象与期待。但与生俱来,对故乡的那种情感,它比此前,留给我记忆的黑白照片相比,更加情浓。然而,在这浓情之后,我又用心浪漫地去行走,定然,别有一番风味绕心头。
“一个人浪漫于北极熊”。其实说穿了,我浪漫于我的家园土地上。我思想的叶片总悄然在宁静的夜晚生长,就像这土地上的一棵树上的叶子,这一片片叶子筋络分明。一根筋络,就是一条流动的河,而河流就是土地的记事绳结。有几多土地,就有几多优美的动人的传说,其中所溅射出的文化氛围,亘古以来就滋养着我们。然后义无返顾地,一段一段变成历史,河流般地流淌于我们的土地。谁敢忘怀土地呢?希腊神话里,安泰离开大地,就失去了力量的传说,清晰地向我诉说背离乡土的悲剧……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瞬息间是夜晚》,对这点给予了凝练的表达:“每一个人/偎依着大地的胸怀/孤寂地裸露在阳光之下/瞬息间是夜晚。”短短几句,往返于这样一组既对立又依存的范畴之中:阳光和黑暗,存在和消逝,生命和死亡。钟爱土地,就是钟爱自己的家园。夜晚殷勤地擦拭我的思想,便擦出一个怎样在故乡的大地行走的问题。那位生前默默无闻、身后却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的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你想要旅行么?要旅行的话,你只需要存在就行。如果我想象什么,我就能看见他。如果我旅行的话,我会看得到更多的什么吗?只有想象的极端贫弱,才能为意在感受的旅行提供辩解……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佩索阿进而揭示了这件事情的实质:“弱化一个人与现实的联系,与此同时又强化一个人对这种联系的分析。”
我就是这样,“弱化一个人与现实的联系,与此同时又强化一个人对这种联系的分析。”正如英国作家康拉德所说,对于艺术家而言,“天下没有一个光明的地方或黑暗的角落不值得投以惊羡和同情的一瞥,哪怕是匆匆一瞥也罢”。同样,一个真正的欣赏者也应该有这份“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同情心,何况我说的是我的故乡。
家园行走,有人问我从何处出发?也就是按现行的说法,线路从何处开始?我不再为一种所谓的线路而费思想,追逐或者划分一条线路,那是很简单的事了。如果我们把被称为“北极熊”的地图划分一下旅游线路,最好是从头部开始。请看这线路,我们就知道它的旅游价值:
西宁——塔尔寺——群加林场(“北极熊”的胡须)——支扎寺(“北极熊”的嘴)——雄先林场(内含堪达寺、嘎夏迪寺、缸山等等,系属“北极熊”的眼睛)——八宝山(“北极熊”的前脊梁)——夏琼寺(“北极熊”的心脏)——青沙山(“北极熊”的前背)——扎巴清真寺(“北极熊”的前腿顶)——李家峡(“北极熊”的左脚及饮水时的流水)——坎布拉林场(“北极熊”踏过黄河的右脚)——公伯峡(“北极熊”的后左脚)——积石峡(“北极熊”的后右脚)——阿河滩清真寺(“北极熊”的后腿顶)——马步芳公馆(“北极熊”的后腿顶)——河群峡(“北极熊”的肚子)——丹斗寺(“北极熊”的后背)——西关清真寺(“北极熊”的后背)——马阴山(“北极熊”高拱的腰际)——瞿坛寺——西宁
从这一条线路不难看出,青海著名的两个寺(塔尔寺、瞿坛寺)都成为起点和落脚点。众所周知,青海地区著名寺庙很多,除了塔尔寺之外,瞿昙寺同样是青海文化艺术画卷里重要的篇章。瞿昙寺位于马阴山下的乐都县,它以辉煌的建筑、精美的壁画、珍贵的文物而著称。瞿昙寺迄今已近年历史,比塔尔寺的历史还要悠久,瞿昙寺的格局是明代宫殿式汉传佛教寺院,院落布局严谨规范,讲求协调、对称、统一的递进关系。塔尔寺有酥油花、壁画、堆绣三绝,瞿昙寺同样有壁画、彩画、石雕三绝。曾经有学者为瞿昙寺感叹:前有敦煌,后有瞿昙,将瞿昙寺提到了敦煌的高度。还有一种说法,“到了瞿昙寺,北京再甭去”,这就是说明瞿昙寺的建筑与北京故宫的建筑风格是一样的。
对于这点线路的选择,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一条未走的路》揭示得十分透彻精辟。一条道路在树林里分成两岔,通往不同的方向,行路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那么,选择哪一条?放弃哪一条?取舍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须如此的特别理由。于是我作这样的选择,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然而唯有这样,才能将西宁、湟中、贵德、化隆、同仁、循化、乐都,这一条连着公路的线路贯穿起来。这只是第一步的选择,因为这条被选择了的道路,不久又接续上了另一条,这个过程还会不断地重复。这样,随着脚步的不断延伸,曾经相交相连的两条岔路,相互之间距离越来越遥远,通往完全不同的区域和风景。家园何尝不是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机遇和偶然性,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面貌。任何一种选择都同时意味着更多的放弃,任何一种实现,也都是以众多其它可能性的夭折作为代价。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就是沿着这一条线路,寻觅家乡的人文精神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风光揽物。当我在青山绿水里穿行的时候,我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老人,看着槐花飘落的叶,和永远不会留下自己足迹的路,黯然失色。浓荫蔽日的群加林场、雄先林场,面目各异的游人和表情温顺的各种林中鸟兽各得其所。所谓“杂树交阴,云垂烟接”、“翠柏烟峰,清泉灌顶”。斑驳的阳光穿透浓密的树叶,给游人的脸上形成迷离恍惚的光斑,令人生出惊讶、惊诧的表情;还有堪达寺的“龙”与“佛”建筑,更让人多了对“佛”的博大、“龙”的精神的深层感悟;八宝山绿色奔涌的波涛、连天接地,离天那么近,其幽深浑厚之气能叫人立刻可以忘却街市的喧嚣。它连绵的身姿,有雄奇劲健之态,又不乏绮丽柔和;在夏琼寺细瞧树上自然生长的一个经文字,我会为产生这样伟大的神奇而震撼,而那些金碧辉煌的美丽所显示出庄肃的典致,因为它的高不可攀,竟让我却步,我是一个无所惧的小人物,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祥睿心态,是前所未有的,心临其境,那些历史画卷一帧帧地在眼前恍惚,使我迈不开脚步,只可仰慕,不可近前抚摸,只是因为那是历史的存据,不容亵渎,不敢随意地拍照。每一次的文明进程,是与伟大的人物分不开的。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宗喀巴的孩子,从小志向远大、聪明好学,年仅十六岁就孤身徒步到西藏求学。有一天,长期游学在西藏的宗喀巴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束白发。宗喀巴手捧白发心中无限伤感,自己当年离乡求学的时候,母亲还是满头青丝,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宗喀巴又何尝不想念母亲呢?但此时的宗喀巴,在西藏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佛学大师,既要忙于研究经典、弘扬佛法,同时还肩负着宗教改革的重任。为了抚慰母亲,他马上回信,请求母亲在他诞生之处,盖一座佛塔,以这座佛塔作为自己的替身,让母亲能见塔,如同亲晤儿面。塔尔寺由此而来,而且塔尔寺只所以成名,缘于宗喀巴。但我大惑不解的是,远比塔尔寺早,更是宗喀巴从小削发求学的夏琼寺,有几人甚至几篇文章曾写过?人们忘记了宗喀巴是从夏琼寺走出去的,是夏琼寺培养了宗喀巴,宗喀巴从六岁入寺到十六岁入藏,他在夏琼寺呆了十年。可不可以这样讲,没有夏琼寺就没有宗喀巴;没有顿珠仁钦就没有宗喀巴。但不知是历史遗忘了,还是信徒就近取名,把夏琼寺反而遗忘了。
但我行走夏琼寺时,不是不想,实在是自惭形秽,不敢率尔操觚,以免贻笑大方。那是一种面对神灵之物,敬之畏之、膜拜有加、不敢轻侮亵玩的心情。在我看来,写这心灵的感受,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那是一种直抵事物核心、洞察存在底蕴的本领。我虽不具备,然而我将目光从寺院上移开,像一条琴弦,被一根手指拨动电脑键盘时,我感觉到胸间某种板滞的东西,正在剥蚀、融化,而一种遥远的原野气息,却慢慢地鼓胀,渐渐地盈满了。夏琼寺建筑乃至墙上一壁,贴有一种精工细雕的灿烂,不由使人惊服古人的智慧。而有些传说,比其它寺院更加高瞻。宗喀巴大师在夏琼寺,刻苦修习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等本尊法13年。值得一提的是,宗喀巴大师在修习本尊文殊菩萨心咒时,他所住房间的墙壁上,经常显印了分明的心咒字迹。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有缘的人,能在其附近拾到带有咒文的石头。并时常有彩虹、雷声等特别吉祥的现象发生。一步步量过前门,那小小的门里经堂,常让我想起宗喀巴求学辩经的场景,浩浩荡荡的众生膜拜,让我无不敬畏历史,是历史,让我们铭记一个人,无论再伟大,它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只是飘起的一纸彩带,而在无限长的过去里,曾有无数的人,都挥起过这纸彩带!而我的步量,也觉得有些无力。走在夏琼寺山上,常觉得自己很渺小,像是沧海一粟般缥缈,那时候的感觉,就如在大千世界里,自己站在天际之间,小,无比的小,那么微不足道。
青沙山上的风马,让我知道什么是神山,感悟一个民族敬重自然的伟大。而高峡出平湖的李家峡大坝,湖中迷人景色,蜿蜒水中的山林坎布拉林场,我喜欢穿着球鞋,实踏着脚,走在山林寺院长廊之间,怀着婉约女人的心情,慢慢地流连,然后披上一件袈裟,露出一个袖长的胳膊,一袭长衣地穿梭于山林寺院之间,如林语堂笔下的红牡丹一样,大方而才气惊异,今生就这样,如一叶飘落的花瓣,点点散散,普普通通,平静地埋没在人海之内消溺……顺路渡步群科古城遗址,依旧是绿树掩映残垣断碑,依旧是斜阳暖照伴几只鹊鸦幽唱。初春时节再次踏进古城遗址,我心中突然有一种回到千古草原的感觉,耳旁犹闻金鼓铁骑之鸣声。如读唐诗宋词中,也爱读凄凉怅惘的吊古伤怀之作,“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更会理解什么是“樯橹灰飞烟灭”,历史在这里,就是一个长长的省略号。如果再经过县城,穿过丹霞地貌的河群峡,让我知道风雨的雕琢,让一座山,如何走向辉煌。公拍峡让我典雅妙致,让我婉约着赞叹,“西电东送”,可能拥有和我一样心情人的感叹……再顺路昂首走在马步芳公馆的甘都中学校园里,定然会自我感觉很好,觉得自己是很美的。这种美丽,有点孤芳自赏的意思。这自我欣赏来自“花园”式的校园,更来自古幽的公馆。阿河滩清真寺濒临黄河,历史悠久,差不多镶嵌在远离热热闹闹的乡区。进入其间,愈行愈静——水幽林茂,杂花生树,野趣渐浓,似有“惊起一滩飞翔鸟”的效果。在积石山下,看着一块块斑驳的石头,一座巧夺天工的玉楼叠嶂,在阳光中永远的闪烁,让我不禁一声长长的感叹,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重要的是,大禹的踪迹和史前文化的诗词,在这里一一呈现。
我一个人浪慢地走着。这是一种极致的行走,这是一种淡然的行走,这是一种追寻的行走,这是一种沧桑的行走,这是一种诗意的行走。虽然其情景、其性情、其姿态,像一只缓慢行走的“北极熊”,全没有像他乡异地行走时,“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回家一问,什么不知”的那种感觉。其间由然而生的境界,是让人无法预料的。所谓的“境界”,就是一种感悟中灵魂的超然。如果往大一点说,西方思想是“有我”的,而中国是“无我”的。中国人以抱一为天下式,西方则没有这个“一”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重以不变应万变。而这里的不变不是绝对的不变,而是“得一”大道上的变化,我曾见过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千山万水千才子”,下联是“一天一地一圣人”,显然,后者略高一筹,这是一个境界问题,而这个境界就是现在的人大多不认识的大化之境,它是靠天地万物化育而成,他应是与众生同体,合天地成形的大象之境。其大为无限大,上不封顶,下不封底,有才者任意驰骋,尚不能触其边角。这个境界可谓正大而光明。“夫缀文者情动而辞生,观文者披文以人情”,“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之一境界。”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的,因此,创设融言、情、境、行于一体的做法,对我的写作是有帮助的。这就是我一个人浪慢行走的理由所在,而且这里的圣人,不仅仅是点燃藏传佛教“后宏期”之火的穆苏赛拔,不仅仅是创立格鲁派的宗喀巴,还有培养宗喀巴的老师顿珠仁钦,还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道风景线。但走着走着,像拉磨的驴一样,绕着圈子。我问自己,这样有什么意思呢?我于是想起那个哲人说过,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然而,我一路走来,我发现这话是对的,每一圈,都有不同的感觉,伴随不同的思想在浮现,迎面而来的是不同的春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物换星移,境随心变,同样的一本书,前后隔了多少年再来读,会有不同的体会。就像一部《堂·吉诃德》,少年看了开怀大笑,中年读来若有所思,老了再来读,却泪流满面。这样的书像一座藏有若干间密室的古堡,开启各个房门的钥匙是不同的年龄数字。一部书倘若具备这样的品性,就不复是那种只在短暂时间内生长的应季作物,而成为一棵贯穿悠长岁月的大树,沐雨栉风,与时间对抗。所以,我总觉得,有时候,我也像堂·吉诃德,西风瘦马,不停前行……就这样,同样的道路,一年四季的走下来,就有了某种哲学的意味,就像朝圣的信徒一样。
我微笑了。一个人浪漫地行走,自然有太多的笔触值得用心来提记,总以为前面的山是顶,奋力而上,登峰而眺,远处高峰绵延不绝,诱惑不绝。坐在山顶,迎风静默,舒爽、惬意,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尽情地呼吸、远望,收美景于眼底,揽晴空于胸怀种,或者神仙的日子就是这样,那么此时的你,就成了人人膜拜的神仙,悠哉,乐哉。那在古城遗址上走过的步履,让我浮躁的心渐渐地平实,也开始拥有了一颗平常的心。
文字节选于北京白癜风治疗价格昆明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sgpxinjiapo.com/dxmp/15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