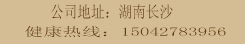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以为山就是褐色的,石头是灰着的。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不知道大地的男根可以如此坦坦荡荡地耸立,而山母之女阴,也可以那么平静而优美地展示。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原来也是可以璀灿绚丽的——曾经一度,我是那么不喜欢有一个与自己禀性和审美取向大相径庭的名字。
我说的是,我遇见了丹霞山,一片红色的群山,一座天生阳元石和阴元洞的奇山。
图/刘加青
先说名字的事吧。也许本来只是文字游戏——我惊喜地发现,我们一行中好多人,其名字一旦与丹霞二字连接,居然都来得那么的妥帖,甚至如沐华光,顿生异彩。“丹霞晓风”,这是台湾散文名家张晓风给丹霞山增添的一缕清新之气;“丹霞丽宏”,上海大家赵丽宏先生为丹霞山贡献的一份赞美显然更是大气;“丹霞乔叶”让年轻可爱的河南女作家乔叶更有一份明丽,“丹霞玉奎”又让山东汉子小说家石玉奎越显豪壮,就连我们都十分熟悉的《散文海外版》前主编甘以雯老师的大名,与丹霞二字放在一起,“丹霞以雯”,虽然不能解释,但不也是意味无穷的么。至于广东本地和来自北京的散文作家李清明和凸凹两位,无论是“丹霞清明”还是“丹霞凸凹”,都是十分恰当和生动的……不一一而赘。
同行诗人王久辛,写诗之余擅弄笔墨,且发挥诗人对词语的稔熟和机巧,给人挥毫题写时,总令人有意外惊喜。丹霞山工作人员中一个清秀的女孩,有一个特别的姓氏“神”——哦,如果没有遇见你,女孩,我真不知道居然还有这样的姓,王久辛也有同样的感慨,只见他大笔一挥而就“丹霞神女”,真是天造地设的契合呵。轮到我了,也是现成得不假思索:“丹霞若虹”——许是太过潇洒和随意吧,宣纸上掉了一滴残墨。我并不在意的,本来就是以字会友,尽兴即可,我不追求完美,我接受瑕疵,这一滴废墨真实地带着在场的气息,更有利于今后的回忆呵。而诗人却不这么想,似有洁癖的近忧,兼具对自己字画藏名山、留后人的远虑,久辛执意重新写,且放出狠话,“你放心,我不会重复的”,稍一凝神,“虹若丹霞”即泻于笔下——字还是这四个字,果然没重复,且还是那么气势恢宏,在场一干人全乐了,我也乐得陶醉于自己的名字被如此美丽地颠来倒去。
说到底,我们都是沾丹霞山的光了。“丹霞”二字有如深谷幽兰、人间芳菲,人只要近之,即受氤氲泽被,立刻染上了它的光辉,各自名字一俟与之相连,即刻灵动,随之人的精神也蓬勃开来。
图/刘加青
思维由此发散,我注意到哪怕一个家常的平常的词汇,只要前后缀以丹霞二字,也立刻多了几分色彩,如开花发芽一般生动起来。奇怪了,难道这俩字就是传说中的众妙之门,只要通过此门即可开出一片新天地?比方说“丹霞人家”吧,就好像比任何别处的人家生活得更为绚烂似的;而“水上丹霞”,能让人生出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奇幻之感;还有“丹霞红豆”,也比其他红豆红得更为热烈和奔放——哦,这可是千真万确、如假包换的事实。美丽的丹霞红豆是当地特产之一,在细细观赏和比较一番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红豆不止是特别鲜艳,奇特处还在于几乎找不出豆脐来,难怪它浑然一体的红得如此饱满!在一家名为“红豆兰庭”的店里,我选购了一件精美的车挂。家里新添的车是一水的浅色内饰,原本配了串缅玉车挂,很是净扮,但有点太素了,换上用丹霞红豆串成的这件吧,那三二平米的车内空间一定会生色不少。
我只能感叹,丹霞二字,真的太神奇了!在丹霞山的几天时间里,我与这两个字时常相遇而每每发呆,总觉得有大美在其中,一时竟未能完全领会。
终于有一天,当登上长老峰的摩崖石刻群,见到高有2.7米,占地跳16平米的气势磅礴而又端庄秀美的石刻“丹霞”二字,我有了一种顿悟。这是在某位书画家的画室里决不能产生的顿悟,这是在某座美术馆的展厅内决不能产生的顿悟,因为与此时此地相比,再豪华的画室也是蜗居,再现代的物馆也是斗室——我是在长老峰半山腰间,头顶青天,脚踩云海,山峦起伏在无尽之头,山风习习于无源之梢。耸立于我面前的“丹霞”二字,镶嵌在质地紧密细腻的红砂岩层中,又被浓绿的植被簇拥,庄严肃穆却又气韵生动。就在那一刻。我豁然厘清了自己的感觉,是的,我感受到这里既有中文汉字之美,也是词语命名之美。
图/刘加青
中文汉字之美,不仅美在其形体,更美在风骨,美在精髓。汉字笔划,横肥竖瘦都有一种肌理感,而左撇右捺的走势,更有一缕脉纹的质地;每一单个字如“丹”如“霞”,本就自有一份内容和神采,组成词之后又别开生面,内涵陡然升华,境界更加崇丽。记得来到长老峰的山腰间,别传禅寺山门外的摩崖石刻前,一行人不由都止步不前。在那里观赏,清谈,合影或小憩。我则面壁多时,细读超大尺度的斗方“丹霞”二字,再读旁边的“耸秀争奇”、“赤城千仞”、“红尘不到”……久久浸染其中,待转身过来时,自觉有所开悟,有所心得,一时间感到清风佛面,身形飘逸,人我几近半仙。
再说词语命名之美。因岩石以红色的砂岩为主,丹霞山之得名似乎其来有自,浑然天成,是一件特别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溯源此山得名的过程,也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在远古时代这里曾被称之为“韶石”,首见于北魏丽郦道元的《水经注》。这很好理解,因为此山坐落于韶关一带,此时它的名字如同一个人的幼时乳名,张家男孩叫“张娃”,李家女儿名“李妹”一般,满不在乎,稚拙质朴。尔后大约在汉代,它又被称作“曲红冈”,因为这里有一条江名曲江。曲红之名,应该是弯曲的江水和红色的山冈的结合吧。比起随意的小名,曲红冈算是学名了,有来源出处,有简略概括。之后这一带群峰还分别分时被称之为锦石岩,锦岩、长老寨、金龟岩……以至现近代作家郁达夫游玩此地后,还以《方岩纪静》来称道它。
顺着这一长串名目细细捋来,我似乎看到前人一次次忖度着,一次次调试着,一次次校正着,不惜花上千百年的时间来给这一人间奇景命名。当地的方志学者和专家们一直在查寻“丹霞”之名到底起于何时与何人,但至今仍然是个无法考证的谜。我却以为大可不必追究了,只要看它的取名轨迹,看看它各个时期的大名小号各个曾用名,我们不难发现,对此山的命名一个比一个生动,一次比一次美妙。要知道,对一件事物的命名过程,其实也是开掘和发现的过程,提炼和升华的过程。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新的美景,新的发现,新的震撼,新的惊艳……日积月累,酝酿发酵,终于令我们的先人中的某一个,灵光闪现,神思飞涌,跨越了地域的限制,抛却了现实的羁绊,升腾到浑然天上人间、不分云朵山体的至高境界。于是,“丹霞”二字如电光火石一般出现,美轮美奂到无以复加——至此,命名完成,这一带的红砂赤壁山岩,得此美名后,竟如获初生一般,重新堆垛矗立于天地之间,让人眼前一亮,刮目相看——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星星又已不是那颗星星,月亮已不是那个月亮。
上帝造物,天工开物,我等芸芸人类,面对大千世界的鬼斧神工,头顶浩瀚星空的变幻莫测,反躬内心丰饶又细微的感觉,能做到的又是什么呢?无外乎就是发现、感知、体认、理解和阐释,而这一系列的活动,若非要以一言以敝之,我以为就是命名了。给天空中的一只飞鸟命名,给山林中的一头走兽命名,给飘忽而过的声音种类命名,给骤然而至的风暴形态命名,给我们内心的种种微妙的情绪命名——比如“尴尬”、“忐忑”就是多么恰当的给感觉的命名呵——命名一旦完成,能指和所指互为表里、合二为一,这个符号和它所象征的意义即告成立和确定,这就是中国古人强调的实至而名归,以及名正而言顺。
好吧我承认,如此强调命名之重要,如此赞叹“丹霞”山名之美妙,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引出一位人物,丹霞山之得名离不开这位人物——他就是地矿学家冯景兰。因为正是他,从专业的角度给了丹霞正式的名号,他是打造“中国丹霞”这一铭牌的第一人。
年,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地质地矿学家冯景兰先生,考察广东地形地貌来到了这里,他被一片红色的山群所震撼。他看到厚厚的岩层被风化侵蚀,形成堡垒状的山峰和峰丛,他看到千姿百态的奇石、石桥和石洞。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特的地貌景观,而这种地貌景观在西方学术著作中——是的,当时地质地矿完全是一门西学——还没有被描述过,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被意识和认知到的地质现象,需要由他来揭示和昭告于天下,而他首先要做的事情即是命名。
感谢苍天和大地,感谢冥冥之中的天意,感谢所有的偶然和必然性,让冯景兰这样一位地质学家来到这里。这是一位有着丰厚的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他当即采用了当了“丹霞”二字而不是别的什么如方岩、锦岩,来命名形成这种地貌的红色砂砾岩层———“丹霞层”。一曲乐章就此訇然奏响,一扇山门豁然打开,一块灿若云霞的地理瑰宝华丽转身,惊艳面世。继冯景兰之后,又有陈国达等多位地质学家在他的发现基础上继续推进,从“丹霞层”到“丹霞地形”,及至最后按照地貌学术用语规范为“丹霞地貌”。这是中国学者为世界地质学贡献一个学术名词,也是中华大地给世界捧出的一块红火的瑰宝。
我素来景仰有才华的人士,而对自然科学领域里兼具人文情怀的专家(反之亦成立,即在其他领域做出实绩的诗人作家),还要多出一层崇拜和敬重。再说冯景兰这清雅的名字怎么有些面熟呢……手指稍稍那么一动便找到了答案,一个让人惊叹的答案。冯景兰何人?他既是一代哲人冯友兰之弟,又是一代才女冯沅君之兄。也就是说,冯氏家族人才济济,一门书香三兄妹,其名字分别在各自的学界——哲学、地质学、文学——流光溢彩。
冯友兰,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创立了“新理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皆是他的著作,如三足鼎立一般撑起了中国哲学史的一片天地,像他这样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在中国寥若晨星。冯友兰的女儿也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学者型女作家宗璞,以其鲜明罕见的风格,在文坛一枝独秀。三兄妹中的小妹冯沅君,是曾受鲁迅称赞的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时与庐隐、凌叔华、冰心等人齐名。而早年在家乡,这兄妹仨就以前后考入北大、前后出国深造被传为绝代佳话,。
诗礼人家,学养深厚,从一门书香走出来的冯景兰,有一副科学的眼光,也有一怀文化的襟抱,当一片红石海洋在他面前荡漾,立即以“丹霞”名之,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地质学家眼里,不仅江山可以如此多娇,科学也是可以如此多娇的。我相信,在“丹霞”之名石破天惊问世那一时刻,专业素养、诗人情怀和天造奇观是同时在他心中澎湃涌动着的。
据已考证的结果,“丹霞”一词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曹丕的诗句“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这只一种景色的泛指。尔后专用于描述此山的如“色如渥丹,灿若明霞”,如“水尽岩崖现,丹霞碧汉间”等,都只是文学性的描写和赞美,都带着形容和比喻的色彩。对于这片神奇的山水来说,这显然还不够。而现在不同了,丹霞在现当代已然又是一个专业词汇,是一个标准的学术用语,它有着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开辟了世界地质地矿学的一方新天地。在学术界,有着这么美丽的专业术语似乎并不多见;在文学界,如此生动的词汇却有着严格科学定义的情形,更是少有。
我以为,这就是文质相符的丹霞命名之美。
离开那一天遥望山门,再次面对“丹霞”二字时,我心里十分纠结。似有三分喜悦,自以为对它有了一番心得体会;更有七分失落——天哪,不远千里来到这里,颇费周章浏览数天,仅才识得丹霞俩字,如同才领到一张入门券。而进得门来,丹霞山大小景点成百近千,古村落星罗棋布、禅宗寺庙闻名遐迩,人文历史积淀丰厚,简直如卷帙浩繁的书册这才翻开首页。好在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只要有所得,都会乐陶陶。我连回头如何炫富的句子都造好了,我会这样告诉别人我去过丹霞山:如果说有一种蓝叫中国蓝的话,我以为那是青花;如果说有一种红叫中国红的话,它就是丹霞。
文/高虹第二届“我心中的丹霞山”全球华文散文大赛三等奖
转载请注明:http://www.sgpxinjiapo.com/dxmp/5886.html